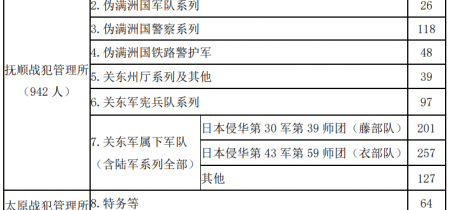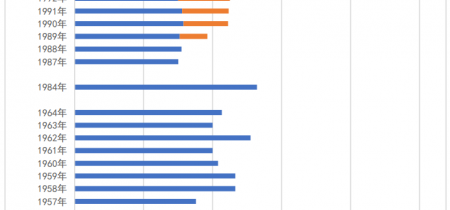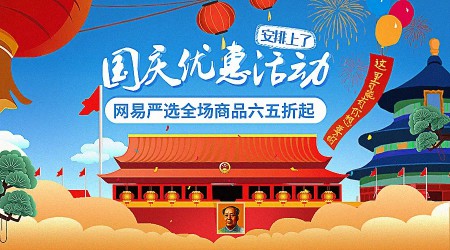栏目: 历史
2022-08-17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中日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交往,不仅有国家层面的各种活动,民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互动也不可或缺。近日,赵京华教授主编的学术随笔丛书 “观日文丛”问世,首次推出的四册分别是赵京华著《思想构筑未来:中日思想文化读书记》、王中忱著《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张明杰著《海东游艺: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以及陈言著《万壑有声:中日书间道》。7月23日,在京相关研究者在鲁迅博物馆院内的鲁迅书店,以本套丛书为切入点,围绕日本问题、中日之间的问题展开讨论。本次座谈会内容丰富,根据内容侧重不同,分篇与读者分享。本文为上篇,围绕研究日本、讨论中日之必要而谈。
作为丛书作者之一,清华大学日新书院王中忱在发言中说,这几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冷战快要结束或已经结束的时候,开始和日本发生联系,并且长期行走在中日之间。而到这套丛书进入筹划和出版阶段时,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他首先抛出问题:在今天这样的时代状况下,这套丛书所讨论的问题,是不是还有意义?应着这个提问,很多学者谈了自己的观点,总的看法是:在今天谈论日本是必要的。这个必要不仅是说今年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上,也缘于中日两国在地理上、文化上“一衣带水”的渊源,以及长久以来的历史纠葛,更在于我们所身处的当下——所谓“变局”,需要我们对“自我”和“他者”有更清醒、更深入的认识。
座谈会上,不少学者分享阅读体会时都指出,“观日”关乎的不仅仅是日本,也在观照中国。“这四本书大部分话题讨论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经由‘日本’所折射出的‘中国’,或者‘中国’与‘日本’的交错、叠合、共通的部分。比如,对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的构筑、日本战后思想史中的鲁迅论、中国东北部区域人文、清末中日书画的交流等。”北京外国语大学日研中心的秦刚说,“但这并非‘观日文丛’名不副实,我认为反而体现了‘观日’这一文化行为的某种必然的路径和指向。在自我认知与重构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个他者存在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思想的很多问题,都无法脱离‘日本’这个他者来认识。既‘观日’又‘观中’,甚至以‘观日’为路径‘观中’,在两者间反复折返,这正反向证明了中日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互为镜像的关系。”北京鲁迅博物馆黄乔生认为“观日”(而非“知日”)体现了作者们老成的心态,面对近乎脱钩的中日关系,如鲁迅的一句诗所说“岂有豪情似旧时”,小心探索、苦心求异、耐心求证。
这四册书,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呈现,事实上是学术研究的结晶,呈现的是中国学者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董炳月表示,“知识界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发声”,即使“个人的研究总是有限的、片面的。如何克服有限性、达到全面的认识?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更多的研究者发声、写作。许多‘有限’放在一起,就是‘无限’,许多‘片面’放在一起,就是‘全面’”。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孙郁,也在发言中主张学者要通过立体的思考打破言说的困境。“我觉得知识界的声音在今天遭遇到许多尴尬的局面。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民众朴素的爱国情感之间,知识人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发声,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我个人认为,我们以前所认可的《联合国宪章》在今天依然是重要的参照,而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识,以及像大江健三郎、丸山升、木山英雄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依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资源。中国知识人应当在更开阔的视野里讨论存在的困境与精神难题。那么东亚的历史的一些遗留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里的复杂性,大家都清楚。而这个现状也提醒我们,在差异性语境交织的今天,研究者叙述历史的简单化思维是值得警惕的。我们在鲁迅以来的知识人的复杂性文本里感到,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世界政治需要有一个开阔的视野,才能够瞭望到幽微之处。”
当“为何谈论日本”成为一个问题时,知识人面对言说的困境,还是要生出言说的勇气。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以“夸父追日”作比,发言令人印象深刻:
“观日”一词让我想起抗战时期周作人写给汤尔和的一句诗:“漫策断株追日没”,他是化用夸父逐日的典故。以观察日本、研究日本为毕生志业者,在我看来,都有夸父逐日的勇气,甘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失败者。
陶渊明诗有云:“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夸父逐日看似自不量力,而陶渊明却认为这种必然以失败告终的志业,有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与文化意义,即所谓“功竟在身后”。夸父逐日这一意象,也似乎暗示着研究者(夸父)与研究对象(日本)之间的关系不是稳定的,二者都处于持续的移动、竞逐中。当我们长期凝视这一对象时,很可能被刺目的日光灼伤眼睛。
今年上半年我在准备一个关于沦陷北平日常生活史的讲座时,丸山真男的一段话让我将历史与当下关联起来,他说从外部看,战争或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一系列戏剧性的打击,但对于生活在那个世界的人来说,只是一步步接受这种变化。每件事、每条新闻都比上一次更糟,但只是糟一点儿,你已经有了某种心理预期,等待着下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幻想到那时候,有人会站出来发声,会形成更大规模的反抗。但是,历史像有自我意志似的,向着大家都不愿意的,而又已默默接受的深渊滑去。这段话一下子击中了我,好像替我说出了历史中人的生活实感。所以对我而言,日本不是作为学术课题而是作为思想资源而存在的,“观日”在今天,需要有夸父逐日的执着,更要有火中取栗的勇气。
于中日交流而言,今年除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外,还有一特别的机缘——今年是鲁迅留日一百二十年。而谈近代中日,鲁迅恐怕是不可能错过的话题,“观日文丛”中有不少篇章涉及鲁迅。
座谈会上,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姜异新即提出重新思考鲁迅的“东亚意义”。她分享了两点思考:
第一点,《思想构筑未来》中提到“二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借助中国的思想资源来思考亚洲,构筑东洋独自的现代性,从而将鲁迅主题化,将其思想资源发挥到极致,实际上也就是将鲁迅作为方法来抵抗西方文明中心论,共同寻找亚洲现代性方案。姜异新说:“虽然‘假如鲁迅活着’是一个假问题,但仍想试问一下:假如鲁迅活着是否会认同日本知识人给他的标签——有着被压迫民族革命经验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生前曾经质疑过:‘东方文化的精髓难道在日本吗?’他也深刻地批评过日本所谓的‘中国通’。尽管日本知识人有着复杂的构成,对此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当我们把东西方对立起来看的时候,不能忘记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时代课题和问题意识。鲁迅在留日时期翻译东欧弱小民族国家文学,动机之一就是力图摆脱日本的影响,而直接步入世界文学之林,并没有强调亚洲感觉和视野。”
姜异新提到的第二点思考与周氏兄弟有关。她提到,1923年初鲁迅在日本人办的报纸《北京周报》上高频亮相,发表自己作品的日译乃至谈话栏目。而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表面上看,那是一个家庭经济事件,本质上却是新文化苍穹下两颗耀眼的明星正冉冉升起,谁也遮蔽不了谁的光芒。‘周氏兄弟’并称五四文坛独有的现象,因这一年鲁迅高调进入日本文化界视野以及《呐喊》出版事件,或将不再,这是否也可引入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研究的维度中呢?”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的刘春勇特别谈了对《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一册的阅读心得,与鲁迅、与东北有关。“我反复读的是他的关于东北亚的书写,”刘春勇说,“在我们固有的知识结构当中都觉得东北是一角,但其实东北是整个世界的起点,同时又是世界的终点。”他认为,中日之间在东北亚的纠缠,可以说是“亚洲腹地”与“海洋”交接的纠缠——日本“南下”可以进入“海洋”,“北上”可以进入“亚洲腹地”。而在一般认知结构中,我们过于“中华中心”,甚至包括鲁迅也是这样。刘春勇谈到,鲁迅在1930年代提到拔都时,甚至包括成吉思汗,都是嘲讽的态度。但也是那个时候顾颉刚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通过战争的契机而扭结起来的,怎么样才是中华民族?怎么样才是中国?当时的知识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鲁迅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想得“小”了。
另外,刘春勇抓住王中忱在《地之缘》中提到的一个时间点——1742年,谈了自己的思考。如果放在整个欧亚大陆来讲,1742年是“礼仪之争”的终点,是乾隆统治的鼎盛时期。然而就在这一年,自利玛窦以来的频繁的中西文化交流被画上了句号,但同时,整个东北亚的(现代)皮毛贸易始也在这一年拉开帷幕。“1742年被称为‘皮毛贸易元年’。伴随着‘贸易’进入的是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大清帝国‘羁縻’政策的失效,而俄罗斯则逐渐控牢了东北亚‘暧昧’之地,日本人则是后来的经略者。”刘春勇说,“所以,东北亚的纠缠就不是一个地方史,也不是一个东北亚的区域史,而是全球史。从这个方面去勾连的话,就打破了我们固有的二元认知结构,使得我们进入到一个暧昧而含混的地带当中去进行非常规的思考。”
资讯来源: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翠果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也可通过邮件或页面下方联系我们说明情况,内容由发布者注册发布,本网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任何单位、个人、组织不得利用平台发布任何不实信息,一切法律后果都由发布者自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