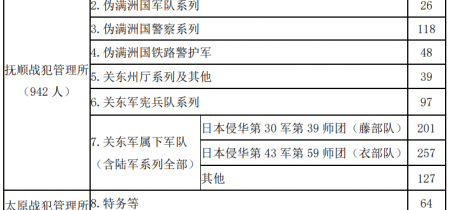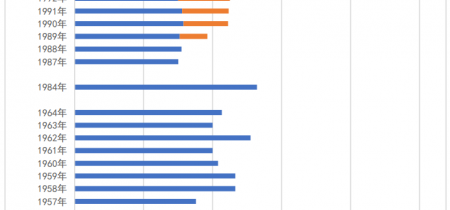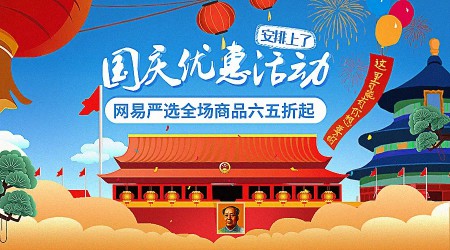栏目: 历史
2022-08-17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中日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交往,不仅有国家层面的各种活动,民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互动也不可或缺。近日,赵京华教授主编的学术随笔丛书“观日文丛”问世,首次推出的四册分别是赵京华著《思想构筑未来:中日思想文化读书记》、王中忱著《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张明杰著《海东游艺: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以及陈言著《万壑有声:中日书间道》。7月23日,在京相关研究者在鲁迅博物馆院内的鲁迅书店,以本套丛书为切入点,围绕日本问题、中日之间的问题展开讨论。本次座谈会内容丰富,根据内容侧重不同,分篇与读者分享。本文为下篇,围绕“观日文丛”的阅读体会和延伸问题,撮要呈现。
这套学术随笔,脱胎于各位的长年研究经验,选题不追随主流,总是从问题意识出发,挖掘常人难见的资料,来补足既有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比如山中商会,经过张明杰的研究,面目逐渐清晰,近代中国文物流失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物盗窃和贩卖的历史过程中,山中商会所扮演的角色,过去我们认为是古董贩子,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它在帝国扩张中所起到的作用,张明杰就提供了多面向的意义。王中忱老师的关于“蒙疆”研究等,有些小文,都是酝酿好多年的作品。这四位让人佩服的,就是都不是为了写论文而写文章。文章很短,但是内涵的发掘过程、考证过程和课题所揭示的价值,却并不亚于长论文。提出问题的过程,让人感觉挖到了真正的矿脉。他们不遵从主流,比如鲁迅研究,已经积累了那么多成果,中忱老师、京华老师、明杰老师竟然还能挖掘出那么多有价值的题目,很了不起。
郭颖(厦门大学日语系):游子·游心·游艺
张明杰老师长期旅居日本,经过日本人文的深度浸润,堪称中日艺术的“玩主”。所以对日本的观察与思考,是一种最切实,最真实的感受与体验。这也正是国内学者比较缺少的,特别是现在提倡的所谓区域与国别研究,仅仅是将日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有别于我国的客体,这样的研究,其实会逐渐忽略掉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关联性,而仅仅以自己的主观标准与皮相的观察,凭借经过人为筛选过滤后的文献与史料,而得出预设好的结论。如此这般,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方法,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菊与刀”式的研究成果。所以,张老师虽然在引言中谦虚的说书中收录的是“大小闲文”,但是,当下被“内卷”催生出的研究中,最为缺少的或许就是这种所谓的“闲”。人类的“闲情逸致”,便是艺术的本源之所在。
《海东游艺》一书,既是张老师研究的内容,其实也是张老师自己的写照。正如书名所示,虽多年身居“海东”,但一直秉承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在延续,“观日”亦在延续。正如丛书封皮的颜色,虽然同为橘红色,但颜色有着微妙的层次,从浅到深,代表了不同年龄层,不同视角的日本观。陈言老师的“声”、张明杰老师的“艺”、王中忱老师的“缘”、赵京华老师的“筑”,虽是不同的切入点,但放在一起,却又能够完美地连接、传承、并延展下去。相信,如果后人也撰写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话,张老师的贡献也定会成为书中的一章。
彭春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全球史、进步史观、经验的重负与体验的悠游
王中忱老师的《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围绕东北方向的“北疆”进行讨论,时间和空间十分开阔。明代开始设立“九边”,这是传统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带。王老师讨论的主要是“九边”东北方向大同、宣化等沿线的地域。王老师讨论的时间段始于14世纪到15世纪之交,这正是西方航海大发现的时期,也是近代全球化的开端所在。但是,如果从内陆的角度来建立全球史,恐怕就要和这一条传统的欧亚大走廊,也就是王老师书中的“北疆”发生关系。
王老师的书,让我感受到了阔大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包括对全球史的新思考。我特别认真读了《张家口:陆地港再开埠与亚欧通道新构成》一篇。随着京张高铁开通,北京、张家口两个城市之间往返十分方便,两个城市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从清河站出发,几十分钟就进入张家口,但对张家口的历史、建制沿革、明代以来的发展,我们还是陌生的。读了这篇文章,很多问题豁然开朗。长城之外,也是中国。长城之外,并不荒凉。此前我和复旦大学的章可老师聊天,他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对张家口特别感兴趣,那里有早期传教士的落脚点。这也提示我们,在思考近代中外交流问题时,要将视野多投向“北疆”,并从那里寻找全球史的突破口。
赵京华老师的《思想构筑未来:中日思想文化读书记》提出中日思想、文学的“同时代性”,让人印象深刻。作者视野非常开阔、涉及的从新渡户稻造、橘朴,到东京审判,再到丸山真男、柄谷行人、木山英雄,拉出了整个20世纪的日本思想史,很了不起。从明治、大正,到昭和、平成,从战前到战后,这整条知识线和思想线,的确达到了以思想构筑未来的效果。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对丸山真男的论述。丸山坚守启蒙、个人自由的价值,他始终对进步拥有信仰。进步,恰恰是一个非常值得再讨论的概念。因为我们现在一谈到进步,很容易就跳跃到进步史观、殖民主义,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的逻辑环节。殖民主义的进步史观的确需要检讨。但从另一个方向来看,人类历史究竟有没有进步,有哪些方面的进步成果,我们未来还要怎样去追求进步,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思考。
陈言老师的《万壑有声:中日书间道》,是一本围绕自身的经验进行讲述的书。这种写法,我自问是做不到的。我基本上放弃了经验、整理日常经验,而是直奔历史的世界,进行理性思考。要把昨天发生的事情,自己经历的过往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复原跟人交往时双方每一个反应、每一句话背后的心绪、情感,对普通人来说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陈言老师这本书直面了现实和自身的经验。比如写和梅娘交往的故事,还原每一个细节,复现细节背后人物的心理和情感,精彩极了。这是文学的魅力!
张明杰老师《海东游艺: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主要是艺术史,我对其中罗振玉的部分相对熟悉,其他题目就比较陌生。感觉张老师在讲述中日文化交流时,和其他三位老师的姿态不太一样,要更悠游一些。赵京华老师提到,“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干戈”。张老师呈现的可能更多是中日两国长久持续的那部分文化关系。
总的来说,这套丛书从经验出发,到历史记述,再到思想构筑,包含了非常复杂丰富的内容。背后蕴含着人的主动性。现在是一个大时代,每个个体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人仍旧是有主动性的,人能创造历史。我们这些多多少少都有日本经验的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专业都受惠于这种经验。除了主动性之外,我们还有责任感。要把我们亲身的经验、对历史的思考传达出去,作为不可或缺的声音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
韩尚蓉(社科文献出版社博士后流动站):“视差”之跳跃与普遍性之追求
所谓的“观日”,既是“观日”也是“观中”,进而中、日对观。这是一个很有洞见的提法,在“观日”时,是站在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一个普遍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面对那些已经被“刻板印象化”的现象保持警惕;在“观中”时,曾经作为“异邦人”的内在经历又使得在面对我国当代种种文化现象时能够带有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换言之,如果不是在中国与日本的“视差”间来回跳跃,是无法获得这种开阔和普遍性的视野的。
在我的阅读中,这套丛书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普遍性”。今天我们谈论日本、或中日,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建立以及建立起了怎样的共识。这一问题长久以来一直缠绕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纠葛中,无论是从晚清起(甚或可以追溯到更早)以亚洲为单位的思考(章太炎1907年前后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还是后来“侵略—反侵略”,抑或是再后来诸多经济文化交流,实际上都是在思考这一问题的延长线上。直到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或许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我想,随着自身环境与外部环境、我们视野的变化,思考的路径、角度却较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以往我们在“东亚”这个范围内部去考察“东亚”“中—日”等,那么对于“普遍性”的追求是否会为我们带来“世界性”的视角,这时再重新回到“东亚问题”或“中—日问题”时,可能又会带来新的理解和发现。
提到“观日”,也就不得不提到“对话”。中日间的对话,是跨越两种不同(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十分近似)思想体系的对话。而一般来说,越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就越能跨越语言的障碍与不同思想体系的对话。我想这也是如今对普遍性价值、普遍性思想不断强调的原因。这可以说正是“对话”“交流”的基石。通过“对话”,通过“面向外部言说”的姿态,来达成一种在交流中普遍有效的情感,也许是当下我们在中日交流中所需要抱有的态度和方向,也是几位老师在丛书中向我们带来的启示,也是我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所要持续保持警惕和关注的地方。
颜淑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建构良性民族主义
几位老师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王老师论述的三十年代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顾颉刚等人创办《禹贡》都产生于面对日本侵略急需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这一具体的语境之中。而赵老师对民族主义的系列论述尤其给了我很多启发,也让我重读丸山真男、竹内好以及鹤见俊辅论述民族主义的相关文本。正如赵老师在书中所言,1945年的战败和美国占领,以及之后相继发生的印度独立、朝鲜半岛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1950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印度召开的第11次年会,到五十年代中期亚非会议的召开,这一系列的背景使得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知识界的思想焦点。丸山真男《日本的民族主义》、竹内好《关于亚洲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亚洲的民族主义》(1955)等文章都是在上述背景下相继诞生的。
竹内好是从绝望反抗的鲁迅看到中国被压迫民族文学中的良性民族主义,而我注意到这种良性民族主义,也体现在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借助“同情”消除种族或国别差异造成的隔阂,实现人类相互理解的主张之中。这里的“同情”,并非指对他者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推己及人,借助想象与他者共情。譬如,有学者指出周作人五四前后的主题实践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同情”展开的,以1918年对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的解读为契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和《人的文学》等文本以及《齿痛》的翻译等都体现了其对“同情”问题的思考。而对周作人新村理想抱有深刻认同的郑振铎、夏丏尊等人也曾在文中表示过类似的主张,作为教育家的夏丏尊更是提倡把学生培养成“有广博的同情的人”。
鹤见俊辅在于战时执笔并于1946年4月刊行的《哲学的反思》一书中,列举“批判”“指导”“同情”三个词来说明战后哲学的作用,并认为“所谓哲学,就是试图同情他人的一种人类意识”。鹤见所说的“同情”,也是在承认别人与自己不同的基础上,通过“尽可能地灭却自己并沉入对方所处的困境之中”,从而与他人产生共鸣,催生连带感。鹤见认为,在战时日本,这种“同情”严重不足:“由于人们有意让试图同情对方国民所直面的困境的意志窒息,结果,人们不会去想,如果自己处在敌方现在所处的特殊状况之下,也会与他们一样对他们战争目的的正义性确信无疑,从而与我们的国家兵戎相见。只有具备这种同情之后,对战争目的的公正检讨、改善以及战争的中止才有可能”。我们可能自然而然会把鹤见的这种主张看成世界主义,但根据《“民主”与“爱国”》一书的作者小熊英二的分析,鹤见的这种主张同民族主义并不对立。《哲学的反思》中甚至说:“虽然过去的日本主义是个错误,但也没有必要突然扭头奔向美国趣味或俄国趣味。理解自己面临难关的特殊状况,维持对他人和他国国民的同情……到了该确立新国粹主义的时候了。”小熊英二结合鹤见1962年所作《脑髓地狱》一文,分析指出鹤见由此开辟出一条“经由民族主义通往国际主义的道路”。鹤见的主张和小熊英二的分析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否能够带来启发,这是我本人今后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汪亭存(清华大学):另类现代性的中日流转与跨语际实践下的近代中国
在现代性的散布过程里,很多现代技术、思想、文化经历了欧亚长轴传播,进而在东亚形成回圈。长轴传播往往在欧洲和率先维新“脱亚入欧”的日本间完成,东亚回圈则多由日本向周边——中国大陆、日据台湾、朝鲜半岛等地扩散辐射。在这一现代性散布过程里,日本对受容欧洲现代文明有所调适,也有误读或“师心自用”处。这种被改造的现代性有其积极一面,也有将现代性之弊放大的一面。而中国在现代的初期受日本影响生成的现代性认识,亦因此呈现出复杂、辩证的样态。
如中国对“nation”概念的接受。日本将“nation”译为“国民”,兼顾了这一概念的政治性与群体性特征,然而这种翻译其实是基于日本作为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国情出发的,将“国民”不加辨析地引入中文语境对于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从概念到实践都呈现出比日本更复杂的特征——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表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现代国家都不可谓不具备结构性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从欧亚长轴传播看,“nation”的发明在欧洲很大程度是为因应民主(“德先生”)诉求而生,而在东亚则因反殖民的现实需要而深具“救亡压倒启蒙”、甚至如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之路的特性;再如,“nation”又被翻译成“民族”,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然而“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这两词中“民族”的区别,就仿佛“美利坚民族”与“法兰西民族”,或“苏维埃人”与“俄罗斯人”间的区别——二者中的“民族”或“人”是否为同一层级的概念,其间有政治学和民族学的哪些异同,这种“误译”又从概念出发给中国近代史的实践和铺展带来了哪些复杂影响?换而言之,我们如何从一个世界范围内以本土立场观察和体认“民族国家”的“限度”和“效度”?
正是从日本作为“现代性长轴传播与东亚回圈”的中转站与节点国家着眼,近代日本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换言之,“观日”有着比“观英”“观美”等更深长的意味。因此,回到历史分叉的地方,在路口向各个方向回望或展望,中日间的“看”与“互看”和视线的交织,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近代中国,也便有着特别的意义。只有从这一东亚乃至全球的视野回看中国,才能在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类文明坐标下历史地、具体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构筑起相对完整的、比例感正确的现代性认知图景。
资讯来源: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翠果
- 下一篇:互联网并不“虚”
- 上一篇:观日︱我们为何谈论日本:“变局”中的“自我”和“他者”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也可通过邮件或页面下方联系我们说明情况,内容由发布者注册发布,本网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任何单位、个人、组织不得利用平台发布任何不实信息,一切法律后果都由发布者自行承担。